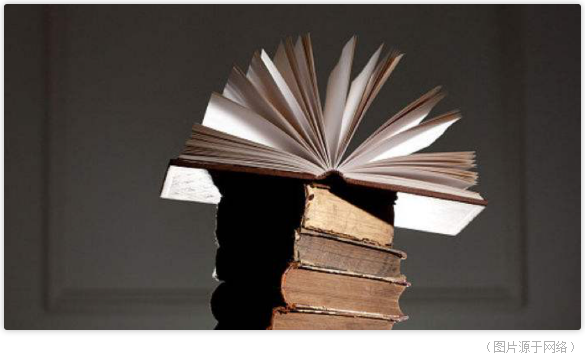内容摘要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具有丰富的国际维度和本土创新。本文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欧美传播理论和对日益媒介化的中国社会的本土研究三个层面,讨论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如何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本文认为至少有三个路径:第一,夯实本土研究,在扎根中国媒介与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经验研究,把握中国问题国际解释的主动权。第二,致力话语创新,一方面要找寻发声空间,抢占国际学术阵地,另一方面要找寻学术伙伴,形成国际学术同盟。就话语体系而言,中国新闻传播理论需要充分挖掘本土文化传统和理论资源,也要充分利用一些欧美主流理论概念,填补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最后,要多维度走出去,包括:鼓励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实质性”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以项目制为核心,推动国内外机构间学术合作;重视“高质量”的学术出版合作,等等。
/ 关键词 /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本土研究;话语创新;走出去
本文从历史出发,简要梳理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国际国内学术脉络,并从夯实本土研究、致力话语创新和多维度走出去三个方面,讨论了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国际影响力的具体路径。
一、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历史性与本体论
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中国理论、中国理论是什么、怎么来的”等核心问题。
总而言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累、引进、反思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并朝着“系统性和专业性”[7]的发展方向快步前进;而这个学科天生的跨学科传统也将开放与包容的视野写入发展的基因,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中,不断获得创新的动力。
二、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三个路径
如何提升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和“理论中的中国”[8]?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路径需要把握:
第一,夯实本土研究。虽然我们要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国际学术视野,但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绝不仅仅是欧美理论的实验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9]因此,中国学者需要集中关注中国社会复杂而充满活力的传播实践,而不是把解释中国问题的理论空间乃至话语权让给域外理论。从历史到现在,从政策制定、文本到实施,从政府到企业到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传统媒体到各类新媒体,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到西部,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从技术到政治经济和各类文化形式,各种关系关联起来会形成各种传播实践的分类矩阵,中国新闻传播学者需要扎根各类关系之中,做到研究的细致入微和脚踏实地,才可以做到知识的有效积累,为回应国际学界有关中国传播实践的问题,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就容易被各类时髦理论牵着鼻子走。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国际学界对复杂而快速变动的中国充满疑问,中国学者只有准备充分解释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理论/信息,才可以消除其不确定性。打铁还需自身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致力话语创新。从争取话语权和建设话语体系两个方面,中国学者需要作出更多努力。
首先,在扎实做好本土研究的同时,要不断扩大与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对话范围和对话深度,充分了解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网络,其中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既有理想也有功利,既有标准也有弹性。换句话说,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并不是中外或者中西想象中的铁板一块,而是充满差异与不平衡。那么,为了争取话语权,中国学者应该怎么做?第一,找寻发声的空间,抢占国际学术阵地。多元甚至碎片化的国际学术界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深度了解中国、中国的媒体与传播实践和中国的世界观——这也回应了理论的本土化本质。因此,需要找到适合的平台积极发声,尤其是涉及上述中国的新闻与传播议题,中国学者决不能缺席。第二,找寻伙伴,形成国际学术同盟。多年的国际交流实践告诉我们,真正认可并愿意与中国传播研究产生关联的国外学术机构和个人并不多。这取决于短期的合作目的和长期的学术旨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和机构需要有所甄别地进行交流合作,在展开广泛而有效的短期合作的同时,更要找寻基于共通的学术立场和学术传统的学术伙伴。
其次,就建设话语体系而言,“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0]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需要做出两种创新:第一,充分挖掘本土文化传统和理论资源,借助其他扎根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丰富自身的概念体系。比如在解释中国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和社会意义时,不是抽象地、去语境化地借用欧美有关social media的一般性理论,而是转向中国的社会交往传统和社会结构特征,从包括乡土社会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中挖掘解释力。再比如在建构中国媒介制度的解释框架时,不是机械地搬用带有“冷战”思维的传媒的四种或几种理论,也不是简单把中国的媒介制度归结为威权主义甚至全权主义,而是转向对中国媒介与政治关系的复线叙事,强调复杂性和历史性。第二,充分利用一些欧美理论概念,填补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在当下交流繁密的国际学术环境中,完全抛弃域外理论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国际学术对话。那么,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中国学者理应明确其适用的范围,在具体学术写作和交往过程中,清楚表明其在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所指代的不同意义。比如,如果商业媒体(commercial media)在欧美国家指涉的是私有的、市场化运作的媒体,那么在中国,商业媒体则仅仅指的是市场化运作的媒体,并未涉及所有权。
第三,多维度走出去。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需要本土研究的基础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支撑,也需要与国际学术界的全方位接触和合作。那么,如何做?首先,要鼓励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以个人或机构身份积极“实质性”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何为“实质性”?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展开了与国际学术组织和各国学者的广泛接触。然而,此类接触多流于表面,更出现了“学术观光团”的戏称,不仅浪费国家财政资源,也徒增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歧见。“实质性”参与强调中国学者以扎实的中国研究为基础,以严肃的学术发表为形式,以通畅的学术交往为目标,步步为营地推进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曝光度和影响力。从学术评价和管理的角度而言,实质性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学术活动需要得到认可和鼓励,否则导向上就会出问题。其次,以项目制为核心,推动国内外机构间学术合作。过去的中外合作多以签署框架性协议为终点,缺乏后续的、可持续性的合作研究步骤,从而与上述学术观光一样流于表面。堆叠的合作协议并不能有效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而“项目制”的国际合作聚焦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建立弹性的合作机制,也有利于锻炼中国学者队伍,提升与国际学术界的黏性,产出实质性的学术成果。再次,重视“高质量”的学术出版合作。建立学术成果的同行评议制度,减少中国学术生产中的官僚主义和圈层主义的负面影响。从中外学术成果互译、联合出版等方面,把注意力从数量转向质量。最后,充分利用多种学术资助机制,通过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设立海外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机构,以及资助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充分整合学术资源,将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打造成一个开放而包容的学术平台。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1]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之一,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不仅要跟进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市场与政策趋势,更要扎根本土研究,尊重多元的知识传统,提炼理论的新思维和新概念,找寻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合作的新路径。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才能知己知彼,找到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空间和发出中国学者声音的最佳时机。当然,这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广泛的学术交往。百闻不如一见,亲身的学术体会才能打破封闭的想象,从而树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性。在关注本土和理解国际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才可能真正实现。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知识创新逻辑。
作者简介: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国际传播分会副主席,德国文明对话研究院(DOC)程序委员会委员。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 参见Zhengrong Hu, Deqiang Ji & Lei Zhang (2016). Building the Nation-Stat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Peter Simonson & David W. Park (ed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Routledge, 2016.
[3] 参见Yuezhi Zhao (2011). “Sustaining and Contesting Revolutionary Legacies in Media and Ideology”, in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01-236.
[4] 比如姜飞,《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以及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0期。
[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6] Nick Couldry and Andreas Hepp (2013).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ume 23, Issue 3, pp. 191-202.
[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8] 来源同上。
[9] 来源同上。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1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